滚动信息2
发布时间:2021-11-16 10:03:40
父亲的决策
15岁那年,我初中毕业。那天,父亲作为家长列席了学校的毕业典礼。回家路上,我拿着卷裹得十分精致的毕业证书,跟在父亲身后蹦跳着。突然,父亲回过身来攥紧我的手一本正经地问我,愿意离开家去外面闯闯吗?问题来得太突兀,又十分严峻,我诧异地看了看父亲凝重的面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久,从布帘那边传来父母间断断续续的对话,我竖起耳朵谛听着:“真打算把小威送到北京去念书?”“他刚15岁,没离开过一天家,你忍心让他去寄,寄……”“寄人篱下……孩子总留在父母身边,太娇惯,不会有大出息……放心吧,亲姐姐还能亏待小弟弟。”“三个女儿都让你送走了,身边就剩下这个根。你的肝疼又越来越重……你舍得,我舍不得……”母亲的抱怨中夹杂着恳求,有些哽咽了。隔了很久,才十分清晰地听到父亲一句语气坚毅、果断的话:“要为孩子的长远想想……”假装熟睡的我顿时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是打算让我投奔北京的姐姐继续学业。
一听说要去北京,我蒙着头在被窝里偷偷乐了。从教科书里获得的星星点点的史地知识,让我迷思着,幻想着。首都、天安门、“十一”游行、毛主席检阅……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
第二天,父亲和我拎着包袱去了市中心的一家拍卖行。一位戴着近视镜的老先生接待了我们。我发现,父亲是用微颤的双手递上包袱请他验货估价。老先生把大衣摊开在柜台上,里里外外地翻动,端详了好一阵子。“是件好东西。”停顿了一下,他说:“要不……你再考虑考虑。”父亲有些犹豫了,抱着大衣一动不动地低头沉思着……猛地,见父亲把大衣重重地往老先生怀里一塞,“出价吧!”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抓住我的手,仰着头激动地喊道:“孩子,你看!”只见一大群鸽子鸣响着洪亮的哨音飞过来。他们映着蓝天,沐着阳光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翱翔着、盘旋着。父亲拉着我的那只手一会儿攥着,一会儿搓着;一会儿紧着,一会儿松着……小小年纪的我哪里懂得,这是父亲在用无声的语言传递着他内心的呼唤:孩子,也去展翅飞吧!去拥抱生活!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
为了我的出行,父母真是操碎了心。母亲最担忧我照顾不好自己的穿戴起居。她匆匆地为我赶制了一件厚棉背心,并让我带走家中最好的一床棉被。母亲在我的内裤里,用密密的针脚缝了小口袋,还在袋口钉上一排按扣。她让我把随身不用的整钱放在袋内,“这样,谁也甭想偷走”。父亲则马不停蹄地给我办转学手续,预购车票。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任何铁路干线。我需要先乘长途汽车到市里,然后坐火车去省城,再转赴北京。旅程的遥远,换乘的复杂,父母的担忧,弄得我也有些畏惧了……
为了能赶上北京的开学日期,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匆匆启程了。临行那天,父亲扛着行李送我去车站,母亲也执意要跟去。阴沉了多半月的天,那天却格外晴艳。一路上父亲始终微笑着畅聊着他小时候是怎样离家求学的,母亲满腹心事地低头跟在后面,一言不发。
汽车缓缓启动了。隔着车窗我不停地挥动着手。就在这刹那间,我似乎才发现父亲高大挺直的身板怎么会有些微驼了,修剪得整齐的双鬓怎么也爬上了稀疏的白发。我的心紧了一下。父亲微笑看着盯着我,用眼神向我告别。我眼睛湿润了。母亲躲在父亲身后,看不见,看不见。远了,远了……
当晚,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简易旅店留宿。能容九个人的大房间空空荡荡。昏暗的灯光看不清墙上的贴画。人生地不熟的我早早就和衣躺下了。我难以入睡。在窗外熙熙攘攘的叫卖声中,在脏兮兮的被子散发的异味中,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孤独,第一次想家……
终于到了!我拎着父亲用过的旧箱子,几乎是一路小跑出了火车站,瞪大着眼睛“扫描”眼前新鲜的一切。按照父亲在家时的嘱咐,我叫了一辆三轮车,操着不着调的北京话,背诵了一遍要去的地址,并反复讯问要多少车费。
“头一回来北京。”“是……”
到了!面对着姐姐家关闭的绿漆大门,我踌躇了。我告诫自己,父亲让我迈出了这一步,今后就只能看你自己的了。抬起头来,勇敢地去面对吧。我走上前去,笃!笃!笃!我使劲地敲响了门…… 李复威
“新”衣
年关,妈妈牵着13岁的我走在县城街头,遇到一对三十来岁的城里夫妇。男的,曾是县里下派的工作组成员,被任村会计的父亲,领到家里吃过饭。他那穿着时髦脚蹬皮靴的妻子,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认真地说,妮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如果穿上呢大衣就更好看了。我听了,说不出的自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臃肿的棉袄看上去像鼓起的蚌壳似的,跟棉被一样的花型说不出的土气。我妈尴尬地笑笑说,乡下丫头哪晓得好看,穿暖和了就好。听了妈妈的话,我更加委屈了,已是中学生的我明白爸妈辛勤劳作不容易,很多想法只是藏在心里不说。
那天妈妈买的大白兔奶糖、核桃酥,丝毫没让我展颜。回家后我扒掉老棉袄,躺进被窝偷偷抹起了泪。晚饭时,妈妈来叫我,我也装作睡着了不理她。妈妈长叹了一声,坐在床边喃喃说,哪个女孩不爱美?妈是过来人,哪里会不懂呢?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打湿了枕头。
衣贩子在过年前一个月,会频繁出现在村里。贩子开着那辆我们叫“乌龟壳”的三轮摩托,驾驶室的挡风玻璃,有几道闪电一样的裂缝,用膏药粗陋地黏住。“乌龟壳”开起来很灵活,曲折的村路,钻子头一样进出,留下一道带着汽油味的烟雾。摊主把摩托车停在村委会门口的水泥地上,卸下车里的衣服,堆在摊开的大塑料布上卖。这些衣服,有八九成新的旧服,有保存不当残破或污损的,也有积压的库存,存在或多或少瑕疵。在城里被嫌弃的衣服,在乡下,依然有受追捧的魅力。旧衣摊前,往往人头攒动,很是热闹。不少人买这样的旧衣过年穿。
那天,一件皮粉色呢大衣,被我妈一眼相住。她一把拎起衣服兴奋地在我身上比量,不料,衣服前肩胛一个花生米大的蛀洞赫然立现。精明的摊主看我妈欢喜的神色骤然没了,眼看商机要跑,急忙朝我妈讲出一串好话:大姐,你瞧这大衣的质地、款式,要不是蛀眼,也落不着我来卖。再说,咱过日子还不是要俭省着才是?那洞眼,拣块花布头缝上就看不着了。我妈摸摸面料,看看衣服针脚细密板实,穿上几年都没问题。在优点的光环下,洞眼的缺憾小到能忽略不计了。与摊主几番讨价还价后,皱巴巴又有破洞的呢子衣,真被我妈给买下了。她先去裁缝店找了块颜色近似的布料补上,小小的补丁,像结痂脱落后露出的粉红新肉,实在碍眼。灵机一动,妈妈拆掉大舅给的一副劳保手套,将米白的棉线在滚水里烫直,晾干又绕成圈,花了两个晚上,织出两片三指宽的绕花织物,在大衣的左右肩胛各镶了一片。破洞被遮掩了,衣服还有别样的温婉。妈妈又从缝纫店借来电熨斗,在盖了湿布的大衣上小心熨烫,哧出的滚滚白烟,如邮轮驶过海面激起的浪花。带着湿漉漉热气的衣服,挺括、神气。它曾经的褴褛,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面打扮成叫花子的黄蓉,是为了考验真心,故意装扮的,当她掀开船篷帘子露出俏丽的面容,小叫花子的印痕一点都没了。
我全程看着妈妈买衣、补衣、熨烫,当妈妈把崭新的衣服让我试穿时,我欢快的心情难以言表。那年春节,穿上呢子大衣的我,笑得如阳光般灿烂,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而这幸福,是妈妈用智慧和勤劳换来的。王征宇
点击“国+社区网”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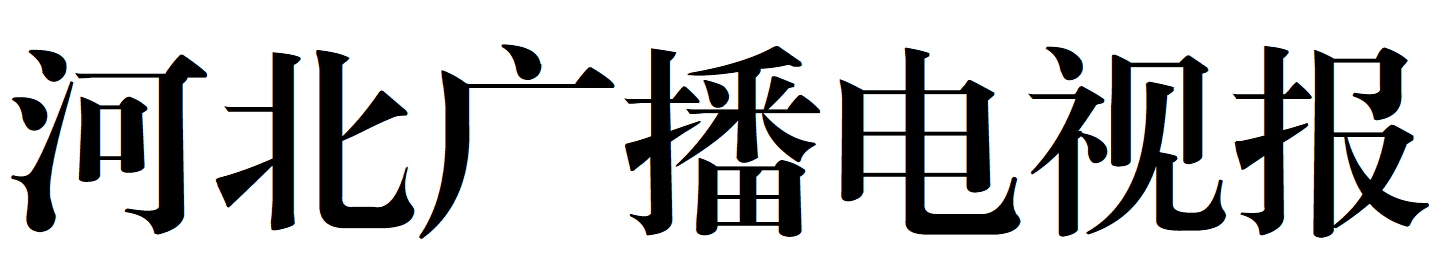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