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信息2
发布时间:2021-06-25 10:53:19
叫不出口的“爸爸”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人就是父亲。他教育你勤俭节约,却偷偷给你零花钱。他责怪你做错了事,却不忍心你被责怪。他从不夸奖你,却早已为你骄傲自豪。父亲是平淡岁月里的超级英雄,最耀眼的星。
在家中,我排行老三,老大是姐,还有一哥一弟。小时候,由于贫穷饥饿,我营养不良,身体瘦小,快到5岁时才会说话。父母忙于生计,对我无暇顾及,让我从小内心孤僻、脆弱、谨慎,但又有一种骨子里遗传而来的倔强。
坦率地说,我和父亲的关系不怎么热切,甚至有些疏远。直到我当兵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的父子关系依然是不冷不热、不亲不疏的,远不及哥弟和父亲那么和谐亲密。造成这样的状况不只是我在家中的尴尬“排位”,或许是我极少喊“爸爸”才是真正的“情感障碍”。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刚会说话时,我是叫爸爸的,虽然不像姐、哥和弟他们那样爱叫、频繁地喊,喜欢缠粘着父亲玩耍交流。隐约记得是在一次吃饭中,快言快语的姐姐好奇地问起来:“我怎么发现,老二(我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二)好像不叫爸爸!”大姐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搞得我内心突突地,慌得不知所措,哑口无言,一脸懵逼。真想不起当时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爸爸严厉地正告家人:“瞎说什么?谁说老二不叫爸爸,都赶紧吃饭,吃完饭该干啥干啥去!”饭桌上的质疑事件最终还是给我带来了影响。“不叫爸爸”传出了家门,传到了街上,传进了左邻右舍的耳中。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我内向的性格愈加沉闷起来,“爸爸”两个字音就像困在内心和精神上的绳索怎么也挣脱不开,叫不出口。越不叫,越不想叫。
父亲经常把弟弟架在肩膀上满院子转悠着玩,也经常带着哥哥到周边乡镇上赶集去,说实话,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找到我和父亲肌肤相亲嬉笑打闹的影子。也许“不叫爸爸”让父亲有些介怀,也许我的性格行事真像母亲所说的很不让人待见。但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的爱都是一样深沉而无私的。这一点儿,我丝毫不怀疑。
我们姐弟四人中,我是学习最认真刻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一个。所以,父亲对我的学习比哥哥弟弟更加关心和重视。为了给我筹集上学的学费,父亲不惜拉下脸面去向亲戚朋友借个遍。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高二暑假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带着干粮和水,口袋里揣着北京二姨写给家里的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出发去借钱。步行,坐长途中巴车,再步行,转乘公交车,再步行。从早晨不到七点出门,直到中午一点多,经过5个多小时、80多公里的奔波和一路打听,我和父亲终于找到了二姨家。尽管我和父亲真诚地说了一大堆话,但结果一分钱都没能借上。现在,依稀记得炎炎夏日的晌午里,我和父亲步伐有力,一边擦汗,一边啃饼,在丰台城乡区域步行找公交的场景。这是我和父亲唯一一次出门的记忆,这个片段,将终生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家有一个“传家宝”——一副老式塑料铁丝腿眼镜,一直锁在一个檀香木制的衣柜里,长年累月用手帕裹放着。听母亲说,这副眼镜的镜片材料是天然水晶石的,拿到太阳底下照射,镜片后聚焦形成的光热可以把一张薄纸燃着。如果眼干、眼痛、眼胀等不舒服,戴上这副眼镜一两个小时症状会明显好转。为此,父母管它叫“养目镜”。
这副“养目镜”在父亲的眼中特别珍贵。小时候,村里“吃公粮”的杨校长经常和爸爸喝酒,一次,父亲喝多了,得意忘形地吹嘘起“养目镜”,之后,杨校长多次找父亲商谈起这副眼镜,甚至愿出300元(当时一年左右的工资)来买“养目镜”,都被父亲断然谢绝了。
1990年底,我穿上了军装。临行的前几日,瘫痪在床的父亲匆忙地吩咐家人找来村里“有头有脸”的几位长辈,说是趁我当兵没走先把家分了,也算了却他的一桩心事。当时,我们家没债务也没存款,只有两处宅院。我们哥仨要分两处院子确实很费脑筋。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上学花钱,从小学读到高中,没帮家里做什么事,哥和弟不一样,早早务农干活挣钱,况且去部队就是为了今后找条出路。想到这儿,我主动提出不要宅院,将来回家有个住处就行。父亲听罢,欣慰地说:“咱家没什么财产,既然老二不要房子,那就把‘养目镜’给他。他上学多,将来用眼的地方肯定多,眼镜留给他最有用处。”这副“养目镜”,不仅是父亲留给我的念想,也是对我无声的激励。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父子永别。如今,我每每想起父亲,努力忆起和他的往事,脑海中浮现他的音容笑貌,还有自己时时想叫又叫不出口的“爸爸”。假如父亲还在,我会把他接到自己的身边悉心照顾,端给他一杯好酒,真诚而亲切地喊声:“爸爸,干杯!”张云华
夏日的西瓜
周末,母亲在电话那头催我回去拿西瓜,说夏天的瓜,她管够。
一提到瓜,口腔仿佛瞬间涌起一股甜汁,从齿间挤入,顺着唇舌,滑进咽喉——那是凭记忆触发的条件反射,因为家乡的西瓜远近闻名。于是,我们马上驱车,回老家,去攫取那份甜蜜。
阳光倾洒如金,故乡在日子的流泻中醒目地蜕变。数条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乡间,两旁全是树。白杨、女贞、紫荆、水杉,高高低低地交织着,好像跳动的琴键。此时,风不起,亦有悦音。那是大地和树木的呢喃,是怀乡之人颤动的心跳,是归乡的喜悦。近了,到了!母亲冲我们招手示意停车,而后忙不迭将我们带到仓库。一张长木桌横着,其上是塑料绳、杆秤,成捆扎好的编织袋;其下有四个竹筐,筐里全是翠皮黑花纹的大西瓜。儿子两眼放光,直接扑上去。母亲选了个模样周正的瓜,用井水洗净后,一刀切下去。只听“咔”的一声脆响,西瓜便露出了漂亮的“内涵”——粉红的瓤,几粒黑白的籽嵌在其中。
“这是8428,甜度高,籽少,爽口!”母亲边赞,边麻利下刀,桌上很快摆了一堆齐整的瓜块。儿子抓起一块就啃,红色的瓜汁肆意地在他嘴巴周围流淌。他圆头圆脑的这副模样,像极了童年时的小弟。母亲和我不约而同地笑了。不一会儿,儿子打了个响嗝儿,拎着瓜皮跑到院中逗黄狗。母亲自从掉了几颗牙后,吃东西需细嚼慢咽。我拿勺子给她,她却摆手,说自己不爱吃,这些瓜全让我们带走。母亲真不爱吃西瓜吗?思绪回溯到母亲年轻时,她喜欢在各个边角地种西瓜。那时,没有空调,大家都习惯在晚饭后乘凉,手摇蒲扇,嘴里啃着西瓜,大声谈天说地。母亲在洗完一家人的衣服和碗碟后,也会加入聊天的队伍,将西瓜的红瓤啃到露出白边才丢开。
过去的西瓜都是露天瓜,天气最热时吃,是解暑良品。后来的西瓜多是大棚种植,品种更迭不断,且上市早。我们年少时,母亲白天经常帮那些承包瓜棚的大户无偿运瓜,晚上用三轮车带回一大堆别人挑剩的瓜。那些瓜,皮厚、不圆,切开来,里面或有空瓤,或有硬结,好在口感还不错。我们成家后,母亲开始学种大棚西瓜,说要让我们每年都能早早吃上瓜。那大棚在4月份宛若蒸笼,人弯腰在里面整藤、授粉,头背腿脚伸展不开,呼吸也不够畅快。好不容易从大棚里出来,身上里里外外全湿透了。瓜成熟时,每摘出一个,母亲都小心抱着,如呵护婴儿。
母亲种的瓜格外清甜。我们安享着这份“福利”,回一次家,装一车瓜。今年照样如此。母亲亲手挑的瓜,沉实圆润,运瓜时需蹲下、捧起,再放入车内摆好。此时,阳光刺眼,周围尽是热气,汗水淌过脖子,沿着手臂、手指,滴到地上。最好吃的西瓜必得经汗水洗礼。母亲的这份甜蜜,更倾注了她对我们无私的沉甸甸的爱。邹娟娟
点击“国+社区网”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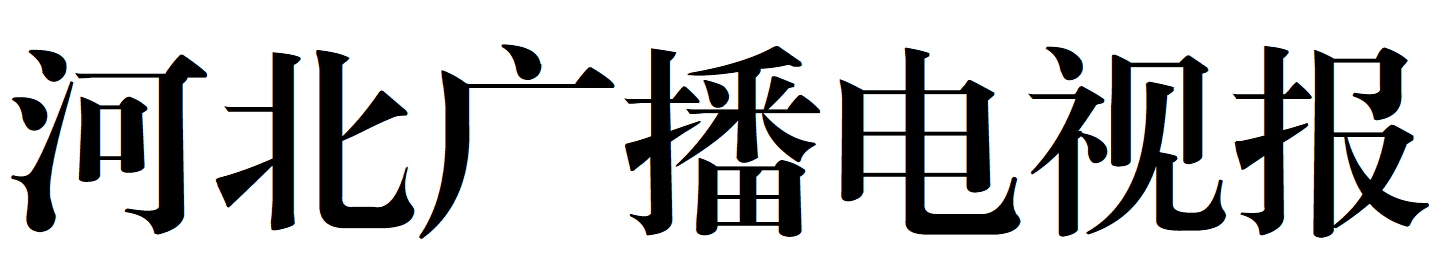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