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信息2
发布时间:2022-12-23 21:20:05

我的老家在河北承德平泉市榆树林子镇果树园村。每次回到老家,我总喜欢挨个屋子转悠,这儿瞅瞅,那儿翻翻,哪怕瞟几眼也心安许多。旧物犹如时光瓷铁,吸纳浮躁喧嚣。沉稳安详属于心灵深处的神色与镌刻年轮的底色,没有什么可以随意改变。
四五把炊帚静寂在柳条篮子里,母亲制作的手艺比不得爷爷,爷爷巧手里的笤帚、炊帚在我的眼中皆为艺术品。一把把笤帚记录了爷爷的一段时光,累叠在一起的笤帚就是爷爷书写的一本书。深厚,繁复,非一日成。
西屋墙角还存有爷爷制作的一把笤帚,孤单寂寞,主人离去了,只有它静静等待不可逆转的命运选择,而它的身后没有同伴,只有空白的虚无。母亲舍不得用这把笤帚,我回乡的几年里,每次挨个屋子转悠的时候都能见到它。当我扫地的时候,手里拎着从集市中买来的笤帚,模样呆板,穗子粗砺,好像水泊梁山李逵的黑胡须,哪里有爷爷制作的笤帚那柔和目光与敦厚性情呢?
记得一次说起爷爷,母亲遗憾地说:“炊帚我还能凑乎弄几把,笤帚一点办法也没有,很多次见过你爷爷刨笤帚,就是学不会。”说得我的眼前便闪现出爷爷坐在西屋炕沿儿、脚蹬系着钢油丝的走杆、双手转动笤帚的情景。我眨巴眼睛,眼角溢出一些眼泪。
爷爷没有向我们说过他制作笤帚的手艺师从何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谁的手里没有几样好手艺呢?瓦匠、铁匠、木匠等等是一种根系在泥土的符号。我的三叔初中毕业闯东北多年,之后抹灰快、平、亮。在手艺人身边,耳濡目染,农村人平时早磨砺出谦逊学习的品行。爷爷不屑谈论这手艺,只有当别人夸他的笤帚物美价廉时,他才附和几句:“那是,我刨的笤帚少说也得用上七八个月的,哪像有人弄的,一看就像病秧子,搁在那儿看着都磕碜。”
爷爷喜欢刨笤帚,一把把笤帚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冬天撵走秋色,田里安静了,乡亲们喜欢这难得的轻松时光。晚饭后,爷爷西屋的灯亮了,我趴在炕梢读书写字,爷爷刨笤帚。爷爷刮高粱穗子的声音格外好听,一只铁平锨飞过,残余的高粱粒子便纷纷落入凡尘。一大把高粱秸褪了叶子,好像春雨刚润泽过,挤挤挨挨坐在木墩上。爷爷坐着小板凳,手扬一根木棒,捶得木墩上的高粱秸断裂成条,锤得声如鼓点。
最初,我并不清楚刨笤帚用的高粱属于另类。秋天,它娉婷袅娜,去田里,一眼就看见它亭亭而立的样子。不过,它穗子上的粒子门可罗雀。我不解为何如此,爷爷的解释简单,多少辈了,都这样,刨笤帚,别的高粱穗子哪有这么宽大的。这常常让我浮想联翩。当我渐渐疏远了农田,反而关注起故乡风物,我慢慢懂得高粱与谷子等农作物心灵深处烙刻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深厚绵长。笤帚同样镌刻深厚的历史文化印记。
高粱有“蜀黍”“木稷”等之名,《说文》云:“稷,齌也。五谷之长。”在远古时期,它尊贵而敦厚,像一位长者。先民的筋骨与思想得到黍稷等谷物温暖的滋养和呵护。
爷爷上过私塾,刨笤帚的空闲,他喜欢哼唱《三字经》等内容,“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的声音依然舒缓在我柔软的心灵深处。他记得不记得、塾师有没有告诉他,“黍稷”与今日高粱之间的千年血脉联系呢?我无从寻找。一代代人心里装着多少后人不知的故事而远逝了。
追溯历史,我们的祖先早就用高粱穗子制作笤帚一类的扫除用具了。夏朝少康以草、竹条制作扫帚,由此开启了先民扫尘净市的文明脚步。在我看来,大者为扫帚,小者为笤帚。我无从寻觅谁是第一个发明笤帚之人,我想,勤劳智慧的先民长年累月与田地厮守,“黍稷”风中轻舞的优美姿态一次次激活了先民的审美情趣,脱粒之后的高粱穗子等沉寂之后则迎来了嬗变。
爷爷与乡村一些刨笤帚的匠人正是这一传统手艺的承继者。爷爷刨的笤帚,穗子犹如整洁干净的毛发,上面鲜见高粱米壳子,以手拂之,纤细的长穗俨如地里不知名虫子双翅摩擦的窸窣,泥土地的气息袅袅飘散。笤帚把儿淡黄色的高粱皮一条条紧挨着,丝线环绕,仿佛拔节而生的厚竹。街坊邻居来串门看到爷爷刨的笤帚,夸赞不已:“你看老爷子的巧手把一堆废高粱穗子弄成了漂亮的笤帚。”“大爷,赶明天你也教教我得了!”“你也就耍耍嘴皮子,明天说不定你又跑到天南海北打工去了,你有老爷子这份专注和细心啊!”
村子里,像爷爷这样刨笤帚的不过两三人,爷爷的手艺最好,时隔多年,回溯一幕幕往事,我甚至以为,在爷爷心中,笤帚是心灵的一种寄托,凝聚着他老人家对土地的爱,对家人的爱。
爷爷年年都种这种长高粱,与玉米套种,两三垄。秋熟时,爷爷赶车拉回那些他牵挂的高粱头,冬闲之刻,灯光柔和,坐在炕沿儿的爷爷脚蹬油丝走杆,一簇簇缀着露珠的穗子宛如兄弟肩并肩,靠在一起。我的耳畔飘过“吱吱吱”的声音,好像听见了夏天田野里攀在高粱叶子上的刀螂的嘶鸣。
有一次,我忽然来了兴致,想试一试身手。爷爷一听,神色诧异,转而兴奋。当我全副武装,手里的高粱穗子怎么也不听使唤,脚丫子也忽然停滞,我没了兴致,好像逃兵匆匆而退,爷爷说,还是好好读书吧!
一年,邻人来家给爷爷拜年,说着闲话,见柜子上一摞摞捆好的笤帚,问爷爷:“你老也不缺钱,八十来岁了,该歇一歇了。”爷爷显出一副并不服老的神态,轻松地说:“我一点也没事,不刨笤帚,尽坐在炕上待着,心都散了。”的确,爷爷快九十岁了还曾去南地拓荒,刨笤帚不过小菜一碟罢了。这是爷爷农活之中的情趣所在,他把缜密细巧的心思都融在了一把把结实耐用、美观大方的笤帚上了,把一辈子与土地的深情厚谊凝聚在了一把把的笤帚上。
逢集,他背着笤帚步行十里去卖。他跟父亲讲:“春天不用你买化肥,我买。”父亲怎么忍心用他这辛苦钱?爷爷叹息道:“你们看我老了是不是?我能干呢,我说的话你们这次得听。”有一年夏天,那时我已离开家乡,忽然接到爷爷打来的电话,他询问我单位需不需要笤帚?“问问就行,别给人家添麻烦。”我问了数目,一百多,正寻思怎么解决,爷爷见我几秒没吱声,说道:“爷爷现在走不动了,要是腿脚像去年那么好,我自己去集市就卖了。”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爷爷去世后,刨笤帚的手艺并没有在父亲手上、我手上传承,父亲喜欢养蜜蜂,我喜欢写作。一次,我在集市上走过,看见一把把簇新而缺乏个性的笤帚,听人说,这都是机械化流水线制作的。我想起了爷爷坐在炕沿儿刨笤帚的温暖画面,耳畔响起了他脚蹬油丝走杆的“嘤嘤嗡嗡”声。
路军
(作者为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榆树林子镇果树园村人,教师,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无论辈辈讲传的英雄神话,无论记忆深处的炊烟小溪,无论东家叔婶的爽直热情,无论西邻兄妹的勤勇好学,每个人都对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或有千般回忆或有万分盼祁。河北广电报业融媒体传播栏目——“我的家乡,我的村”邀您真情讲述:可一段故事、可一个物件、可山水草木、可亲容笑颜、可前豪气悲歌、可今振兴壮迹……
征集热线:0311-87111403
邮箱:251939185@qq.com
微信:国+社区网
抖音:私信国+社区
快手:私信国+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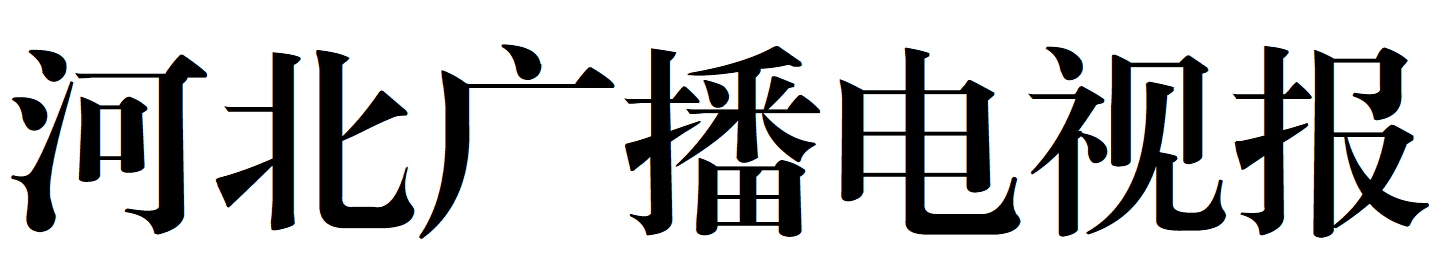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382号